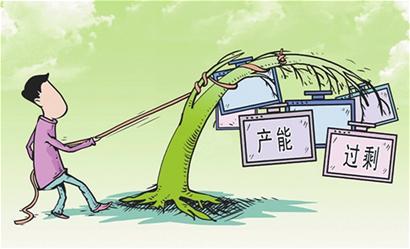
产能过剩一直是近年来中国产业发展的“痼疾”。
产能利用情况最为直接的指标即为产能利用率( capacityutilization),被定义为长期均衡中的实际产量与最佳生产能力之间的差异。美国、日本等国家很早就开始对产能利用率指标进行工业统计和跟踪分析,是用于反映工业经济实力和工业经济走势的一个主要月度指标。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,一般产能利用率80%~90%较为适中,而低于80%意味着存在产能过剩,而低于70%则存在较为严重的过剩问题。2012年底,我国钢铁、水泥、电解铝、平板玻璃、船舶产能利用率分别仅为72%、73.7%、71.9%、73.1%和75%,明显低于国际通常水平。
产能过剩在我国已存在多年,但近期我国正进入新一轮产能过剩,呈现与过去产能过剩不同的三个特点:一是涉及的面比较广,产能过剩具有普遍性,由传统行业向新兴行业蔓延,无论是属于高耗能的电解铝/钢铁制造,还是新兴产业的光伏太阳能和风电,以及早床和钢铁业中高端产品的硅钢,均被业界公认为“产能过剩”;二当前产能过剩具有结构性和体制性特征,有些产业面临长期绝对性过剩问题;三产能过剩化解更具复杂性,化解难度更大,还伴有大量的在建产能。
今年1-3季度,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0.2%,比上半年加快了0.1个百分点,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55.8%,大大高于第1季度的30.3%,表明中国经济对投资的依赖过度和更趋严重。于是原来停建的高铁项目纷纷上马,早已立项而未动工的项目,如广东湛江的钢铁项目也已开工。特别是房地产投资比重过大,占总投资的25%,房屋销售也比较活跃,仍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。房价也在一线城市带动下继续上涨,地王频现,也与宏观调控的目标和要求相背而行。
需要特别指出的是,与消费和净出口不同,投资在当期构成总需求的一部分,而建成投产,就转化为新的总供给的一部分,因此,投资的结构直接决定着产业结构和经济效率。如果投资于供给不足的部门和产品,那么就能增加供给,满足社会需求,缓解供求矛盾;如果投资于供过于求的部门和产品,那么就会加大产能过剩,造成巨大浪费。从我国目前的实际来看,很多行业和产品都存在着严重的产能过剩,而对投资的过度依赖,使得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。
产能过剩的发展使企业的投资预期下降,其解决需要合并关闭一些工厂,这会导致失业,打击居民的收入和消费预期,由此使经济增长面临越来越明显的下行压力。在企业层面产能过剩影响使得企业净利率降低,负债增加,应收账款增加,导致银行不良资产增加,进而将风险传递到银行业。产能过剩已被认为是今后5年新一届政府宏观调控中的最大挑战。
未来有三大顽疾需要攻克:
其一,如何实施行业准入管理。纵观汽车、钢铁、水泥和电解铝等产能过剩行业,本该需要较高的行业准入门槛,现实却是地不分南北都在搞,以至于出现缺水的地方建钢厂、缺电的地方建电解铝厂的现象。
其二,如何突破金融体制。在中国以大银行为主导的金融体系中,信贷资源优先流向大企业、大项目。谁能迅速将规模做大,谁的融资能力就越强。在此导向下,“圈地—融资—上市”的游戏屡试不爽。
其三,如何从根本上让地方政府摆脱GDP情结。产能过剩是市场经济的常态。但在我国产能过剩除了市场外,还有体制机制、发展方式等方面的原因。一位中钢协领导曾感慨,地方政府在钢铁行业发展中的推手力量很强,“在广东,省里支持广东钢铁集团。到了韶关市,就支持韶钢集团。到了区县就支持底下的小厂。”究其原因,还是个GDP情结在作怪。
